渔业统计:
可靠性及其政策含意
粮农组织渔业部
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中国在其统计中高估了1995-1999年期间海洋渔业捕捞量,此统计数据已经上报并由粮农组织公开发表。该论文认为,如此得来的结论是全球海洋渔业捕捞产量,秘鲁鳀除外,可能从1988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而不是统计数据显示的保持相当稳定。根据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论文作者的观点,这将导致人们低估世界渔业的退化状况,导致政策与投资决策失误。这个问题又相继被若干报纸和互联网媒体所提及,包括经济学家杂志。在提醒更多公众关注可靠的渔业统计数据对于渔业管理与监测的重要性的同时,这些文章中也包括了一些误解。这些误解涉及到(1)粮农组织对中国统计数据的理解、(2)粮农组织在全球渔业统计中作用、(3)中国渔业产量的高估对全球渔业管理建议、政策及渔业对粮食安全的贡献的可能带来的后果。特澄清如下:
1.
粮农组织的理解这不是第一次有科学家“发现”中国渔业统计数据高估产量。事实上,一些中国科学家此前也谈及过该问题。粮农组织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农业与渔业统计数据,并在与中国一同核实这些数据。1997年中国在粮农组织的协作下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随后肉类产量统计数据得到修改并下调整25%。普查与定期系列统计数据中耕作面积相差达37%。粮农组织的中国谷物库存数据也已被修改。
根据渔业产量和贸易统计计算出的人均食用鱼品供应数量与入户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之间的明显不一致大概在六年前就开始扩大。粮农组织当时曾提请过中国负责部门-农业部渔业局注意该事宜。此后,双方联合召开数次会议、派出考察团并组织研讨会(例如2001年粮农组织研讨会)。在2001年4月召开的上一次研讨会上,已经认识到该问题并建议了若干后续行动来研究其各个方面,为可能补救行动奠定基础。粮农组织已经与中国一些机构共同建议了一些后续行动,包括2002年在一个县建立示范抽样统计数据收集计划。而且粮农组织还要进一步对上岸的未加工鱼数量进行评估,这些鱼直接用作水产养殖饲料,并被认为数量很大,而且目前被错误的理解为供人食用了。因此说,粮农组织知情并一直在采取相应行动。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分析使用了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根据官方数据对中国和其它具有相似生态系统特征国家的沿海单位面积产量进行比较。多年以前,粮农组织就在较小的规模上用相似的程序来处理非洲国家的类似问题。这两个研究均需要很多假定条件并要大量调整不确切数据,因此被粮农组织认为是类似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附加指标。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太平洋分析研究的统计异常显示图在2001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展示。按粮农组织专家的观点(Caddy等,1998),“若建议进一步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估算方法,粮农组织的数据最好是作为一个趁势指标和研究假定条件的基础,在单独开展的较小规模或同类捕捞区域的更准确分析中加以验证。”
2.
粮农组织在渔业统计中的作用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论文有关的很多新闻消息错误地认为粮农组织只是接收来自各国的数据,而不对其做任何可能的核实与完善。尽管这样的说法可以轻易地减小粮农组织对其发布的数据中的任何错误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毕竟与事实不符。粮农组织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a)促进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利用;(b)编制统计手册与软件;(c)培训统计官员;(d)发展与提高国家统计体系(如最近在非洲和地中海很多国家开展的活动);(e)(通过机构间渔业统计工作方协作)促进全球在渔业统计和制定统计规范方面的合作;(f)从国家和区域渔业机构、国际捕捞注册机构、渔业产业(例如销售与贸易数据)收集各种统计数据;(g)在内部一致性、种类识别和趁势异常方面对收到的数据进行第一个层次的核查;(h)就异常情况咨询有关国家;(I)在年鉴和互联网上公布渔业不同方面的统计数据,并收到用户广泛的反馈。因此,如果出现明显的错误,如果从区域渔业机构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如果成员国同意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各国权威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通常是得到修正的。如果成员国对粮农组织的咨询不予反馈,则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将被单方面采用。当成员国对可疑统计根本不提供支持性解释时,偶而,其报告的统计数据被搁置,粮农组织的统计将被公布。如在本文其它部分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在与粮农组织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报告是粮农组织渔业统计数据库的主要但非唯一的数据来源。在数据丢失或被认为不可靠的情况下,粮农组织根据任何来源的最佳可用信息,如区域渔业组织、项目文件、行业杂志或统计插值分析,来确定将采用的统计数据。在船队统计中,粮农组织用其它来源,如国际捕捞注册协会的数据对各国报送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关于(影响捕捞能力的)技术进展的信息则通过若干专家组提供。国际贸易统计是从各国获得,并通过粮农组织建立的区域政府间机构综合网络(GLOBEFISH系统)进行补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粮农组织全面修改了其拥有的时间序列渔业产量统计数据,包括利用计算机向回计算到1950年,填补不全的数据,按捕捞区域分割数据,考虑政治形势的变化(例如新国家的出现),调整种类标识(因为分类法的变化),完善水产养殖与捕捞渔业产量的区分。由此而产生的成套数据,如用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和大量其它分析中的数据,已经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广泛提供(FishStat +)。
由粮农组织编写并出版的全球种群状态回顾并不是以捕捞量统计数据作为首要信息来源,因为常有比捕捞量更为直接的反映资源状态的指标。所利用的主要信息是直接来自粮农组织的一些工作组和非粮农组织区域性渔业组织(RFOs),及其它正式机构、科技文献(例如科学杂志、学位论文等),并得到来自产业杂志的信息和独立渔业信息,如贸易数据的补充。在非粮农组织区域性渔业组织不存在之处,如在西北太平洋,可以依赖(例如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双边评估活动。当某数据,例如抛弃量不存在时,可能利用咨询专家或通过专门的专业咨询在一次性(one-off)的基础上(例如Alverson等,1994年)进行估算。在一些领域,粮农组织没有手段开展有效工作,例如非法捕捞,根本就不存在全球性信息。如果存在,也只是特定区域或特定年份的数据。粮农组织捕捞量统计数据的一个大的优点是其覆盖范围的全球性,而且具备1950年以来的全部时间序列,并定期更新,因此被用于提供区域渔业总体趁势(例如粮农组织,1994年),并在数据不充分时提供资源状态指标(例如粮农组织,1997年)。
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与维持国家渔业统计体系的财政支持实际上是在减少,而误捕与抛弃、捕捞能力、非法捕捞、船只公海作业授权,经济数据(成本、收入、价格补贴)、就业、管理制度、种群数量及渔业与水产养殖等的统计需要却在大幅度增长。
虽然粮农组织已经付出努力,但是可用的渔业数据仍不能做到完全可靠。从覆盖范围、及时性和质量看,现在的产出远未完善。数据报送到粮农组织时常滞后了一或两年。在单个种类水平上确定捕捞量的比例通常随时间而减少,而随着渔业多样化及大型种群被耗尽,公布的“种类未确定”的百分比在增加。种群评估工作组是一个很好的筛选捕捞数据的工具,但由于缺乏人力及财政资源,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种群评估频率下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数据可用性的总体情况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小型渔业的统计数据仍然令人担忧,仍然缺少很多重要数据,如经济与社会数据、抛弃量,捕捞能力。其结果是,虽然如同与全球发展趁势或气候变化(Klyashtorin,2001年)的良好相关所显示的那样,可用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可靠地反映总体趁势,但是年度数据及评估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年与年之间的微小变化可能不具备统计意义。
粮农组织渔业部相信,与各国共同努力是改善渔业统计,首先满足国家粮食安全和渔业管理需求,然后满足区域渔业机构和粮农组织需求的唯一办法。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渔业管理和政策制定,并会在国家和区域水平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3.
管理、政策及粮食安全上的含意媒体上认为统计误差向政策与产业部门发出了错误信号,已经导致政策及投资决策错误,而且必然引起自满情绪。以下内容将说明上述观点是误解的产物。
3.1 全球种群状况
有人认为,统计的潜在错误可以影响到人们对种群状况的“认识”。粮农组织强调,为了对全球种群状况作出准确评价,例如粮农组织(1997年)出版的种群评价,粮农组织主要采用了直接评估的结果,并以捕捞量数据分析作为补充。这些评估结果是从区域性渔业机构工作组、国家情报中心、科学出版物以及不明出处的文献报告中收集而来,并补充了一些辅助性信息。在这样的前提下种群状况时间序列(图1和图2)和典型状况(图3)才得以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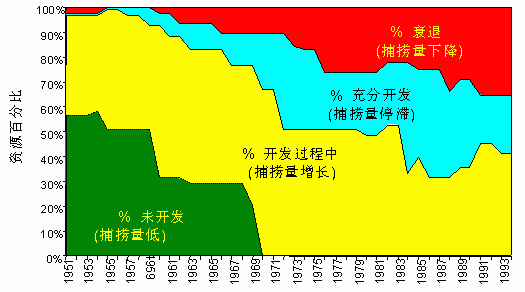
图1:世界资源状况的演变(1950-94年),
仅以统计变化趁势为依据
(Grainger与Garcia,1996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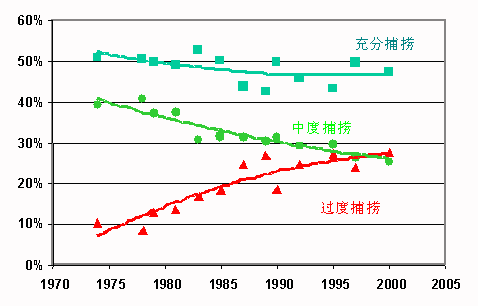
图
2:世界资源状况的演变(1974-1999年),主要以种群评估结果为依据
(Garcia与De Leiva Moreno,2001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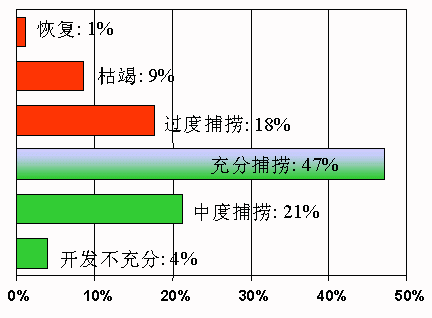
图
3:1999年种群状况(Garcia与De Leiva Moreno,2001年)在全面核查粮农组织渔业生产数据库之后,进行了两个系列分析
(Grainger与Garcia,1996年;Garcia与Newton,1997年)。第一个(Grainger与Garcia,1996年)探索性的分析显示出数据与众所周知的渔业及产量历史之间惊人的一致性,特别是显示1950年以来过度捕捞发展过程的生动和特别的图形(图1)。第二个分析使粮农组织开发了一个世界渔业生态经济模型(Garcia与Newton,1997年),该模型第一次说明了:(a)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最贵重种类的全球过度捕捞情况;(b) 世界潜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经被开发殆尽的事实,(c)数量巨大的补贴可能已经用于维持以30% - 50%过捕能力作业的世界捕捞船队。这应该证明的是,尽管存在某种潜在的中国产量数字误差,但是全球种群的总体下降趁势和世界渔业的不良经济表现已经十分明显,粮农组织已经说明并提请成员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公众注意了。事实上,这些结论已经被科学家广泛引用,被媒体再次利用并被所有重要的非政府机构使用。进一步具体地考虑西北太平洋区域的情况,中国统计可能的误差大概只会影响被中国及其邻国捕捞殆尽的种群的评估。粮农组织研究了该地区以及其它捕捞区域的变化趁势,并从单位面积大陆架产量
(Caddy等,1998年) 的角度及生态学水平(Caddy and Garibaldi, 2000年)进行了分析。Caddy等(1998年)证明了区域性产量下降趁势,并为其提供了一些解释。粮农组织还出版了中国科学家(陈,1999年)的报告,该报告证明中国的很多海洋资源已被严重过度开发。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文章作者不仅借口中国的“误差”改动了世界捕捞量,而且从捕捞量中删除了大规模的秘鲁鳀捕捞量。虽然秘鲁鳀捕捞量的真实性未受到质疑,但是删除的原因据称是秘鲁鳀捕捞量人人皆知波动会“隐瞒”下降的趁势。这种武断的作法加剧了世界数据库的中国偏差可能带来的产量下降的程度,而引发的“下降”又被当成一个新事物展示。实际上,粮农组织在
1994年(Garcia与Newton,1997年)早已经提出了远洋和半远洋大型种群波动带来的问题。粮农组织证明,从总产量中减掉多数被用于制作饲料的五种主要波动种类(秘鲁鳀、智利马鲭、日本和美洲沙丁鱼以及阿拉斯加鳕鱼)捕捞量后,大型、高价值种类的上岸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开始下降了,而且这些种类从那时起已经出现全球性过度捕捞,。自然杂志上提供的“消息”只是确认了一条多年以前已经存在的来自粮农组织的信息。这些分析清楚地说明,尽管数据中可能存在误差,但并未掩盖全球趁势,而且最重要的结论已经形成。这些发现,连同在区域和国家水平上的发现已成为
1990年以来管理和制度变化的基础。
3.2 粮食安全
有人辩称潜在的误差可能误导粮农组织公布的人均食用鱼供应量及渔业对粮食安全贡献的全球趁势。食品安全取决于供应量(产量加上进口量减去出口量)、可用性(贸易)与可获得性(购买力),与粮食总可用量(包括谷物与肉类)有关。因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容易地转换蛋白质来源和鱼的种类,因此“鱼”,不论是野生或是养殖,粮农组织通常视其为单一商品。把“鱼”与肉类和其它食品分开考虑会使解释变得复杂。仅分析一个食用鱼来源,不论是来自内陆、海洋或是养殖产品,会进一步降低这个信息在粮食安全范畴内的意义。但是,直至这个问题被明确解决时,才可能从绝对或相对(人均)量方面分析海洋捕捞渔业对粮食安全的贡献,不论是否包括中国数据在内。就绝对量而言,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如果包括中国的统计数据,全球趁势表现出微量但持续增加,反之不包括中国统计数据时,则呈现稳定趁势(图4)。与后者一致,粮农组织已经声明的就是世界海洋捕捞渔业供应是“稳定”的。但就人均量而言,如果包括中国统计数据,趁势呈现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人均供应稳定,反之不包括中国统计数据时,则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人均每年供应量(从1986年的11.8公斤到1999年的9.3公斤)下降2.5公斤(在这个期间内用于人类食用的比例保持稳定在72%左右)。后者说明,不包括中国在内,世界食用鱼类捕捞渔业产量的增加已经不能够接抵偿人口的增加(在该期间内增长率23%),并且根据粮农组织报告(粮农组织,2000年),该声明甚至适用于包括水产养殖在内的食用鱼总产量。在解决粮食安全需求时,水产养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满足未来需要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粮农组织已经警告,“在一些国家(例如加纳、利比里亚、马拉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平均膳食中含有的鱼蛋白质低于七十年代。(粮农组织,2000年)”与一些媒体报告中的断言相反,粮农组织并没有“自满”。尽管数据方面存在困难,但是该组织已明确的阐明,食用鱼类产量虽然保持明显稳定,但尚未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并且,粮农组织警告,在一些地区人均鱼蛋白质供应已经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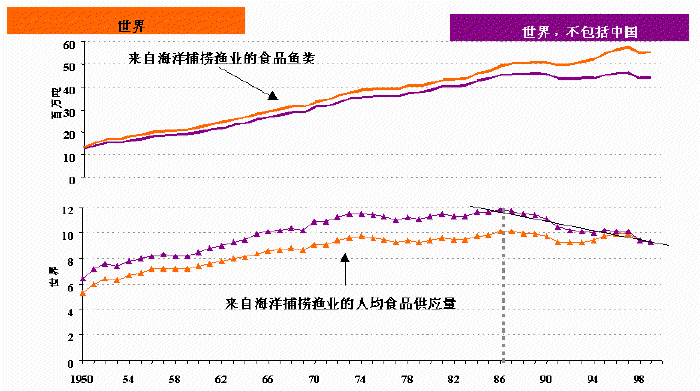
图
4: 包括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绝对与人均海洋捕捞食用鱼产量 (1950-1999年)在未来的二十或三十年中,目前与未来水产养殖产量、环境影响、气候变化、人口增加、经济财富的数量与分配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粮食安全在全球水平上的潜在影响要超过中国报告中可能误差的影响。但是,如果这样的偏差能够被确认并改正,海洋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将确实降低。但是,应该强调的是,与有些断言相反,只有在中国食用鱼出口与进口量与产量相比很小时,中国渔业产量的任何高报才会影响中国目前蛋白质消费量和未来供应计划
(虽然中国确实进口大量鱼粉用作动物饲料,并用于水产养殖,而且出口绝对数量大而且在增长)世界捕捞量相当大的比例被加工成鱼粉(
30%,与某些媒体报道相反的是,其中少于三分之一被用作水产养殖饲料),未知但是可能很大的数量被用作水产养殖鲜饲料(尤其在中国),以及大量的抛弃(每年大约2000万吨)同样可能成为人类消费食用鱼的潜在储备,尽管不能确知目前各种用途可能发生有效改变的程度。未来更大的限制因素可能是购买力(和贫困)而不是鱼的供应能力。可能令人不解的是,尽管水产养殖和过渡捕捞对环境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而且考虑了所有故意和无意的统计错误之后,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的总体贡献在中期似乎没有受到明显威胁。但是关于资源状况和粮食安全状况的两类信息不应混淆。资源不良状况目前应当受到严重关切,而且本来应在过去二十年期间得到实质性纠正。渔业和水产养殖对食品供应的全部贡献尚不令人担忧。由于对外贸易扩大和价格上涨,对于世界人口的最贫困阶层而言,未来的可利用量令人担忧。由于污染不断加重以及养殖技术不适当,未来海产品的质量也令人担忧。所有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在目前和不远的未来都还不是全球性的,其相关的仅仅是某些局部
(国家或国家以下)水平、某些生产制度、某些地区以及某些人口阶层。例如,粮农组织在《2000年世界渔业状况》(粮农组织,2000)中就提出警告,非洲人均鱼供应量一直在下降,如果非洲国家不能更好地管理它们的资源和(或)增加水产养殖产量,那么未来鱼的供应将会进一步下降。然而,毫无疑义的是,全球海洋捕捞量下降已向各国、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该信息要比粮农组织从
1990年初就开始不断重复发出的信息更强烈。中国在数量、趋势和种类方面的统计偏差,如果存在的话,需要查明。同时,正如《2000年世界渔业状况》(粮农组织,2000年)所做的那样,大部分粮农组织相关分析都采取一个预防性措施,将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分开介绍。3.3 对政策和计划的影响
总的来说,渔业资源监测和管理以国家或区域为基础(例如在区域渔业机构框架之下)进行。如果确实存在统计错误,也主要是对中国的渔业资源产生可持续性或粮食安全方面直接实际的影响,或者是对西北太平洋区域,一个相对小范围区域内共享资源产生影响。
全球性统计资料已被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
(COFI)和其它全球性论坛采用。尽管数据存在一些不足,但在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联大,这些数据为各国在制度变化方面的努力提供了辅助条件。联合国渔业种质资源协议、粮农组织依从协议、粮农组织操作守则以及其四个国际行动计划是该行动在全球范围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以政府最高层和产业部门认识到渔业存在的问题为基础,也确实没有反映出粮农组织方面的“自满”。一些可操作性的决策,例如私有部门投资、补贴的性质、决策权力下放、远距离船队捕捞准入协议等,都是在国家一级,以当地的考虑为依据制定的,与粮农组织所提供的任何全球状况无关。但是有人称粮农组织统计资料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影响”决策者。希望这个说法至少部分正确的,不过请记住,随着渔业的发展,粮农组织信息是(括号内是主要相关年份):
这些信息仅代表粮农组织全球渔业信息的一小部分样品。成员国至少部分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使
1982年海洋公约(1994年)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议(2001年)实施生效;通过了粮农组织依从协议(1993年)和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1995年);根据这些法律文件调整了各国法律;通过并开始实施预防性措施;接受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渔业管理原则;通过了四个国际行动计划(捕鱼能力管理、鲨鱼捕捞管理、减少长绳海鸟误捕、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并将考虑制定一个改善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行动计划的可能性。关于渔业状况和趋势的客观和可靠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努力促进可持续渔业和实施行为守则的基础。尤其是关于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报告,对有效地制定政策,有效地进行渔业管理以及对鱼类种群和渔业进行生态和经济监测都是十分重要的。有关状况和趋势的信息,以渔业统计为其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其编撰及传播的方式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粮农组织已就这些关注做出的反应,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来克服现行方式的不足。为了这个目标,粮农组织还将另外在2002年召集一个改善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的技术磋商会议,并将继续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以增强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还可能制定一个改进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的国际行动计划(IPOA)。
可能认为所有这些成就依然不足以改善总体形势,而且所有各方面都面对挑战是强化政治意愿和承诺、能力建设、资源筹措和实现平等。尽管如此,大部分观察员认为在渔业范围内已经取得的成绩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因此,没有理由去伪称中国统计数据高估导致粮农组织成员国制定错误政策。这些决定的成果是否与期望相一致有待观察。
结论
在然杂志发表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报告之后发表的大部分文章认为,由于向世界公布了世界最重要捕捞国家之一-中国提供的错误捕捞统计数据,粮农组织已经
(1)扭曲了全球渔业状况;(2)扭曲了寄予渔业对粮食安全做出贡献的期望;(3)导致政策、投资导向和决策错误。上述信息,仅仅是粮农组织网站和其它出版物中可用信息的很少一部分,就可以证明在全球媒体上的断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粮农组织从来不认为“当地捕捞渔水域资源枯竭可以通过在更远的区域开发新捕捞区域来平衡”和“种群是稳定的”。相反,粮农组织认为过高强度的捕捞正在从北半球向南半球扩展,并始终警告成员国注意由此在全球渔业体系总体可持续方面带来的后果。不准确的统计数据掩饰了“形势的紧迫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样紧迫性已在粮农组织分析中披露,并已被成员国所接受,最近形成的一些国际渔业法规就证明了这一点。引起这样大规模国际标准化行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确实是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发出的紧迫性信息。认为“大部分养殖鱼所喂饲料主要成份是鱼”的观点虽然次要,但也是不正确的。食草鱼和软体动物约占世界水产养殖生产量的90%。
在2001年10月雷克雅维克大会上,粮农组织近期总体情况报告中的几条引证(Garcia与De Leiva Moreno,2001)说明了这种观点。粮农组织称经过五十年特别快速的地理拓展、技术进步之后,年捕捞量已增加数倍,海洋渔业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随着大部分渔业资源或被过度开发,或被开发殆尽或已经被深度开发,现行渔业体系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粮农组织并未强调捕捞业产量的任何增长。相反,它指出报告的捕捞量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达到约8000万吨,此后始终在8500万吨左右波动,到了九十年代年增长率几乎下降到零,表明按照现有捕捞方式,平均而言世界海洋捕捞生产已到达极限。粮农组织进一步指出,过去二十五年中,全球过渡捕捞种群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尽管其速度可能略微下降。该信息证实了粮农组织在七十年代初期作出的估计,即全球海洋渔业潜力约为1亿吨,其中仅8000万吨适合实际捕捞。粮农组织,还指出,资源状况及产业统计数据的质量需要大幅度提高,以便对管理工作的状况进行更好的监测和评估,现有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过渡捕捞种群比例的上升及过度捕捞在全世界海洋范围内的蔓延。
关于粮食安全预测,鉴于鱼类供应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粮农组织考虑的是所有来源的食用鱼,包括水产养殖。粮农组织称“鉴于海洋捕捞产量停滞不前,除非更有效地管理海洋捕捞渔业和进一步发展水产养殖以提高产量,否则来自海洋捕捞渔业的人均供应量可能会有较大下降”。粮农组织强调未来来自捕捞渔业的人均食物有效供应可能减少。
粮农组织当然也认识到:
(1)渔业统计以及统计数据采集程序需要得到实质性改进(也包括水产养殖);(2)由重要生产国家引起的数据扭曲,不论是否故意都会扭曲全球统计数据,并影响公众舆论;(3)然而对于国家和地方决策而言,全球统计数据可操作用途有限;(4)未来渔业对粮食安全的贡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数据质量的长期进步只有通过与各国和区域科技和统计机构的合作方能实现。粮农组织也赞成有透明度,并为其开发的可自由进入的信息系统而自豪。这个信息系统允许来自任何方面的分析人员进入、再处理数据并形成他们自己的结论来弥补粮农组织自身分析能力的不足。
不同于大众媒体,粮农组织作为政府间国际机构,必须以平衡的方式对待“新闻”,并用符合政府间机构地位和功能的方式和语言来提供统计、分析和发出警告。通常认为,可能过于乐观,各方将对此能够予以客观的理解。
参考资料
大陆架地区渔业产量已经超过最高水平了吗?对大陆架产量历史趋势的一些看法。
Caddy J.F.、F. Carocci、S. Coppola (1998年)。J. Northwest. Atl. Fish. Sci., 23:191-219页。
世界海洋捕捞生态学成份的显著变化:根据粮农组织捕捞数据库做出的分析。
Caddy, J.F.、L. Garibaldi (2000年)。海洋和沿海管理,43(8-9):第615-65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资源开发管理状况。
Chen, W. (1999年),FAO Fish.Circ., (950):第60 页。世界高迁移性种类和跨区域种群状况回顾。粮农组织(
1994年),FAO Fish.Tech.Pap., (337):第74页。世界渔业资源状况回顾:海洋渔业。粮农组织
(1997年)。FAO Fisheries Circular, (920):173页。200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粮农组织(2000年)。粮农组织,罗马142页。亚太国家农业统计的改善,粮农组织,罗马。中国国家粮食和农业统计系统研讨会论文集。
1999年9月23-24日,中国北京。第I 和 II卷:项目GCP/RAS/171/JPN的实地文件第2/CHN/3号。粮农组织(2001年)。全球海洋渔业回顾。在
2001年10月1-4日在雷克雅维克召开的粮农组织-冰岛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大会上发表的论文,Garcia S.M.与I. De Leiva Moreno (2001年)。全球渔业捕捞的现状、趋势和前景。
Garcia S.M.与C. Newton (1997),全球趋势:渔业管理。美国渔业协会研讨会,美国马里兰州 Bethsda 20, 3-27页,E.L. Pikitch, D.D. Huppert、M.P. Sissenwine (编辑)海洋渔业历年上岸量纪录
(1950-1994)。趋势分析和渔业潜力。Grainger R. J.R.、S.M. Garcia (1996),FAO Fish.Tech.Pap., (359):51页。气候变化和商业捕捞的长期波动状况:预测的可能性。
Klyashtorin, L.B. (2001),FAO Fish.Tech.Pap., (410):86 页。| 1 | Watson, R. and D. Pauly (2001): Systematic distortions in world fisheries catch trends. Nature, 414, 29 November 2001: 534-536 | |
| 2 | The Economist (2001): Global fish stocks: Fishy figure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001: 99-100 |